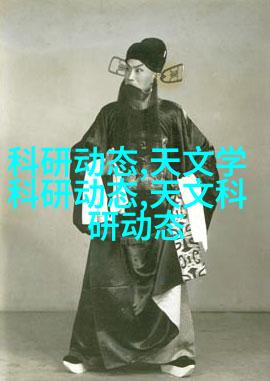毛树德一些天文轶事
●●●
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却关系到生死。
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术氛围对于一流院校来说就像空气对于人类一样重要。 然而学术氛围中的科研要素却很难定量评价。 它不像资助项目和发表论文的数量那么直观和定量可比,因此往往不被重视。

图1 普林斯顿大学天体物理系佩顿堂:一栋优雅的两层建筑(地上一层,地下一层)。 以下是我敬佩的教授和四年来的美好回忆,拍摄于 2015 年 7 月 17 日。
这些年来,我参观过国内外许多研究机构和天文机构,我能明显感受到两种完全不同的状况。 有的机构关闭,大家互不交流,无聊感油然而生,而有的则不然。 。
以我多次访问过的英国剑桥大学天文研究所为例。 该研究所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首任所长是弗雷德·霍伊尔教授,其工作堪比诺贝尔奖[1]。 天文研究所每天上午和下午都有茶歇。 大家自发地聚集在一个开放的空间进行学术讨论,其中包括许多英国皇家学会的成员[2]。 热烈的讨论场面足以震撼每一位参观者。 浓厚的学术氛围向你扑来。
我的母校普林斯顿大学天体物理系也是一个学术氛围浓厚的地方。 1988年至1992年攻读博士学位。 那里的学位。 当时,博士学位。 当时该系只有15名教授,相当于学生总数。 四年来,每位教授平均指导一名学生。 研究生的前两年,我主修基础课。 课程不多,不过五门课(恒星物理、星际空间、星系动力学、高能天体物理、河外天文学/宇宙学)。
此外,每个研究生每年还需要准备两份前沿报告,一份关于理论天体物理学,一份关于观测天文学。 其余时间,学生每学期将在不同导师的指导下进行研究,完成相应课题并发表。 经过这样的两年,学生往往可以深入了解天文学各个领域的知识和进展,明确自己的兴趣和专业,然后选择合适的博士论文题目,最终完成博士学业。
和剑桥大学天文研究所一样,普林斯顿天体物理系每天下午3:00也有茶歇,有很多教授和学生参加。 大家都习惯一边舒服地喝茶,一边严谨地讨论科学问题。
这些年来,很多事、很多人都渐渐淡出了我的脑海。 只有茶歇时的一些讨论还记忆犹新,比如关于1987A超新星的讨论。 当时有人声称1987A超新星产生了周期为半秒的脉冲星信号[3],但从理论上讲,这样快速旋转的脉冲星不应该或几乎不存在,因为巨大的离心力会撕裂星体。中子星破碎(见附录)。
大家对公布的观察结果都很困惑,茶歇期间也有很多讨论。 系主任杰里·奥斯特里克教授也加入了讨论。 面对众人的询问,他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应该是噪音。”他突然说道。 停顿了一下,他补充道:“如果不是噪音,我有三种理论上的解释。” 有趣的是,这个所谓的“半秒脉冲星信号”最终被证明是错误的。
随后,杰瑞一边喝茶一边开玩笑说,他在《自然》上发表的所有文章也是错误的,因为《自然》往往追求新闻效果,缺乏足够的研究,所以不能盲目相信。 喝茶的时候,你可以听到教授们就尚无定论的话题进行激烈的讨论,这个过程往往比上课更有益。

图2 普林斯顿安静的研究生宿舍(研究生院,作者2017年7月拍摄)
说起杰里·奥斯特里克教授,他在天文学界以思维敏捷、口才出名(有人说诡辩)。 我做了他半年的研究助理,时不时地和他讨论一下。 进门之前我常常相信他的错误和疏漏,但出来之后我就被他说服了。 经过如此多次的重复,最终往往很难达成共识(但后来的观察表明,他提出的“BL Lac天体是微引力透镜效应造成的”理论确实是错误的)。
我仍然记得第一次见到杰里·奥斯特里克教授的情景。 那是1988年的秋天,我怀着不安的心情拜访了他,希望能在他的指导下开展一些研究项目。 他问我:“你想做什么?”、“量子宇宙学”。 我回答。 他愣了半分钟,才说道:“这一篇比较难,除此之外,你可以从我一百多篇文章中任意选题。” 经过半年的文献研究,我选择了一个关于微波背景辐射的题目。
当时天文学家通过火箭实验发现,微波背景辐射的能谱偏离了黑体辐射(见图3左)。 Jerry Ostriker教授恰好有一个理论可以解释这种偏差,所以他建议我计算一下。 不幸的是,当我刚到美国时,我对计算机很着迷,在这方面花费的时间很少,进步也很慢。 更不幸的是,这个课题还没有完成。 1990年COBE卫星发现它之前的观测结果是错误的。 微波背景辐射光谱显然是完美的普朗克黑体光谱(见图 3,右)。
这次合作不成功的部分原因可以归咎于科学的不可预测性,但我对此深感遗憾。 直到2004年,我和另外两位天文学家终于与他合作完成了一篇关于引力透镜和暗物质底层结构的文章。 终于,我们解除了遗憾,实现了与他合作的愿望!

图 3 左)Matsumoto 等人。 (1988) 用火箭观测到的微波背景辐射的能谱。 其中,黑点2和黑点3明显偏离温度为2.74K(负270.26摄氏度)的黑体辐射光谱。 右)COBE卫星观测到的能谱是完美的普朗克黑体曲线; 黑点是数据点,红线是普朗克曲线。
除了Jerry Ostriker教授之外,该系的其他教授也都是天文学领域的领军人物,包括我的导师Bohdan Paczynski教授(我又写了一篇文章纪念他[4])、James Gunn教授、Richard Gott教授、其中,詹姆斯·冈恩教授是天文学界唯一一位能同时兼顾理论、观测和仪器制造的全能科学家。 据我了解,在仪器制造方面,他参与了帕洛马天文台双色摄谱仪和哈勃望远镜(WFPC)上仪器的设计。 也正是他制造的五色相机保证了2000年斯隆数字巡天项目的成功进行。
目前,基于斯隆数字巡天项目的文章和引文有数万篇。 该项目已成为天文学史上最成功的巡天项目,并将在几十年内对天文学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 另一位教授理查德·戈特(Richard Gott)对詹姆斯·古恩教授的评价非常贴切:“如果末日到来,世界上只剩下古恩教授是唯一的天文学家,他也可以恢复和重建整个天文学。”
James Gunn教授的妻子Jill Knapp也是该系的教授,在观察方面取得了很多成就。 当我申请普林斯顿研究生院时,她恰好负责该系的招生。 她警告我美国官僚主义的严重性,很早就粉碎了我美好的幻想。 他们彼此相爱,几乎每天都在同一时间上下班。 有一次,他们并肩坐在系楼前的石阶上,仰望星空。 这真是一段无尽的浪漫啊!
理查德·戈特也是一位传奇教授。 他很健谈,可以聊几个小时,这让很多学生很无奈。 因此,如果需要见他,大家都会选择快要下班的时间,或者提前和其他同学约好定点“赶去帮忙”。 他是相对论和宇宙大尺度结构领域的专家,我有幸与他合作撰写了一篇关于宇宙拓扑的论文。 也正是他与北京大学李立新教授一起发现了利用宇宙弦可以实现时空旅行。
有人开玩笑说时间旅行对其他人来说可能是不可能的,但戈特不同。 他是全能的上帝(Gott原为德语,意为“上帝”)。 有一次,办公楼前的一棵树被雷击断了两半。 大家开玩笑说:“这可能是上帝的警告,因为我们把宇宙学弄错了。”
除了这些享有盛誉的教授之外,普林斯顿大学天体物理系每周三还邀请国际知名学者进行学术讲座(座谈会)。 这是一个拓展知识面的宝贵机会。 几乎每个教授和学生都会自愿参加。 学长们还警告我,一定要去看学术报告,哪怕是睡在那里。
事实上,费曼在书中多次提到的著名天体物理系首任系主任亨利·罗素教授就是一个听课时打瞌睡的典型例子[5]。 这个优良传统显然得到了很好的传承。 据我在读博士期间的观察,当时的系主任Jerry Ostriker教授每次听报告都几乎睡着了。 然而,令人惊奇的是,报告一结束,他就能立即醒来提出问题,而且问题往往尖锐、切中要害。

图4 普林斯顿拿骚街的Hoagie Haven店| 资料来源:twitter.com/hoagiehaven
除了学术讲座之外,物理系的学生经常邀请演讲者共进午餐(Wednesday Lunch,Wunch),餐食通常是从普林斯顿知名餐厅 Hoagie Haven [6] 购买的三明治。 大家不遗余力地利用午餐时间,一方面向主讲人推销自己的工作,另一方面打听物理系以外的信息。 我参加过很多次这样的晚宴,印象最深的是S. Chardrasekhar教授、James Binney教授和Peter Goldreich教授。

图5 Subrahmanyan Chandrasekhar教授(1910.10.19-1995.8.21)| 资料来源:芝加哥大学
钱德拉塞卡教授在芝加哥大学工作。 他是Jerry Ostriker教授的导师。 他因发现白矮星的质量上限而获得198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据说,他在教学时创造了班上所有成员(李政道、杨振宁,包括他自己)都获得诺贝尔奖的“奇迹”[7]。 他一生兴趣广泛[8],工作方式也很奇怪:在某个时期只专注于一个领域的工作,解决问题并出版专着,然后转向下一个领域,然后再也没有涉足之前的领域。
有一次,钱德拉塞卡教授访问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时,两名印度研究生极力邀请他参加我们的午餐会。 大家都很兴奋。 和往常一样,大家依次介绍了自己的工作,期待他的评价。 结果他只是说了一句“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然后开始专注地描述自己手头的工作。 当时,他正在研究牛顿的《自然》。 《哲学的数学原理》,其中高度赞扬了牛顿[9]。 不得不说,他的言行透露着一个学者的孤傲和傲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的话至今仍让我铭记在心——对科学永无止境的追求。 科学)。

图6 牛津大学James Binney教授| 作者摄于2017年3月30日
加州理工学院的另一位教授Peter Goldreich也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在行星形成、动力学和脉冲星原理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 午餐会上,他坦言,科学研究常常会碰壁,碰壁也不必气馁。 无非是换个话题或者换个研究方法而已。 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我踏上了漫长的科学研究之路。 每当我遇到困难时,我总会想起他的话,使我能够保持初心,坚持到今天。
我们还邀请了牛津大学的 James Binney 教授参加我们的午餐会。 他的《银河天文学》和《银河动力学》相当受欢迎,几乎天文学界的每个人都拥有一本。 James Binney教授知识面广,可以在午餐会议上对每个学生的作业进行详细点评。
后来,我受邀去牛津参加一位博士生的毕业答辩,再次见到了James Binney教授。 英国博士答辩(viva)委员会通常由一名外部考官和一名内部考官组成。 在答辩之前,每位教授都会写下自己的评语。 答辩时,学生可以在5-10分钟内对自己的作品进行简短的总结,重点关注提问部分。 教授可以就论文中的任何内容提出问题。 答辩结束后,两位教授共同撰写答辩书和综合评语。
在英国,参加学生的博士论文答辩,从论文研究到评语撰写,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报酬却很少,大约150英镑。 相比之下,国内防卫往往只是流于形式。 但即便如此,不少教授仍然反映,英国博士文凭的价值正在逐年下降。 当时我担任博士生的外部主考官,而James Binney教授恰好是博士答辩的内部主考官。
答辩时有一个小插曲,正当我们聊得很开心时,他突然一拍头,“哎呀,我忘记穿学位服了”,立刻大步带我去了他的默顿学院,获得了学位袍,终于保证了合规性以及辩护的有效性。 辩护过程中,他精神抖擞,不断提问。 三个小时过去了,仍然没有停止的迹象。 我最终不得不打断他,这也算是拯救了辩护的学生——现为剑桥大学教授的瓦斯里·别洛库洛夫。
2017年3月底,James Binney教授作为中国科学院国际杰出学者,应邀访问国内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 当我受邀到清华大学做报告时,快到报告时间了,我看见他从远处大步向我走来,就像三十年前匆匆脱下学袍的他一样。
几年前,我在加州理工学院遇到了吉尔·纳普教授。 她告诉我,“讨论是我们天文学家必须做的事情(我们天文学家所做的就是谈话)”,这让我颇为感动。 毕竟,我们这些天文学家并不是急功近利的商人。 我们一生想要的,就是留下一些可以流传于世、可以载入史册的作品。 我们周围良好的学术氛围以及互补专业的讨论非常重要。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大部分天文研究机构和机构能够敞开大门,让每一位来访者都能以开放的心态感受到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浓厚学术氛围,虽然这应该是一个天文研究的基础。科研单位永远保持活力也是成为世界一流的关键!

附录

让我们考虑一颗质量为 M、半径为 R、旋转角频率为 ω 的恒星(见图)。 在旋转坐标系中,恒星表面的粒子会受到两种力的作用:引力和离心力。 为了保证脉冲星不被撕裂,引力(F)必须大于离心力(F'):F=mGM/R2 ≥ F'=mω2R , ω=2π/T ,其中 T 为时期。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对于脉冲星来说,M≈1.4太阳质量=2.8*1030kg,R≈10km,则T≥1ms。 除非质量很大,或者半径很小(这需要特殊的状态方程),否则自转周期很难小于1毫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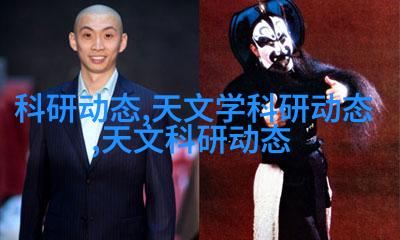
参考文献:(上下滚动浏览)
1.
2.马丁·里斯(英国皇家学会前主席)、理查德·埃利斯、马克斯·佩蒂尼、安迪·法比安、罗伯特·肯尼卡特和唐纳德·林登-贝尔。
3.Murdin, P. 1990,《自然》,347, 511。
4、赛天文学先生,《博赫丹·帕钦斯基教授逝世十周年》,毛树德
5.“如果罗素教授睡着了——他无疑会睡着——这并不意味着研讨会很糟糕;……”摘自费曼的“当然,你在开玩笑,费曼先生”
6.
7、后来发现这是一个误传。 事实上,另一位著名的天天物理学家唐纳德·奥斯特布罗克(Donald Osterbrock)也在课堂上。
8、详情见; 他的研究领域包括:恒星结构、星系动力学、辐射传输、等离子体物理、流体和磁流体不稳定性、椭球平衡图、黑洞数学理论,还有下面提到的牛顿的研究。
9. S. Chandrasekhar,“面向普通读者的牛顿原理”

毛树德
《知识分子》主编
毛树德,教授、博士生导师,《知识分子》主编。 1987年考入李政道先生主持的CUSPEA项目,次年赴美国。 1992年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天体物理系博士学位。 博士后期间曾在哈佛-史密森天体物理中心和马克斯·普朗克天体物理研究所工作; 2000年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留学,2006年晋升教授。2010年回国。现任清华大学天文系主任。 主要研究方向为星系动力学、系外行星搜索、引力透镜和暗物质研究。
制作编辑|卢卡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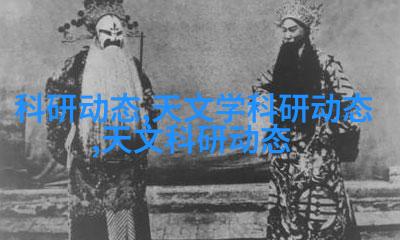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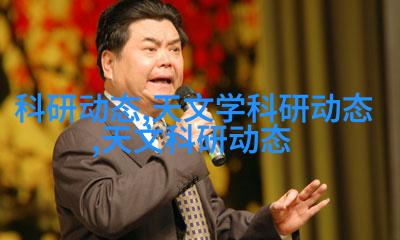
结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