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天文的浪漫是意想不到的
阅读提示:学习天文学确实让你有机会用天上地下的各种望远镜“看星星”; 但更多的时候,天文学家做着看似困难而复杂的理论研究、模型构建、数据分析……但这些并没有阻止年轻人的热情和好奇心。 在他们眼里,天文学的浪漫有着不同的内涵。
“仰望星空,探索宇宙的奥秘,是多么浪漫啊!” 这可能是很多人对天文学的美好想象。 学习天文学确实让你有机会用天空和地下的各种望远镜“看星星”; 但更多的时候,天文学家做的是看似困难而复杂的理论研究、模型构建、数据分析……
但这些并没有阻止年轻人的热情和好奇。 在他们眼里,天文学的浪漫有着不同的内涵。

学习天文“颠覆三观”
“在进入大学之前,我对天文学了解不多。 这让我在开始学习天文学时不会像天文爱好者的同学一样感到幻灭。” 经过10个天文学本科、硕士、博士学位,经过多年的学习,现为中科院上海天文台博士后研究员的赵珊珊笑着回忆道。
她原本想报考物理专业,但最终报考了南京大学天文专业并开始学习。 她发现自己所学的课程与物理学并没有太大区别,而且还开辟了从天文角度认识世界的新视角。 “如果你抱着‘每天用望远镜看星星’的梦想来学习天文学,你一定会失望的,因为实际上你主要学习和使用的是数学、物理和计算机编程。” 赵珊珊告诉《新民周刊》记者,这些课程都非常难。 有些科目的不及格率高达30%。 “我花了很大的力气才跟上进度,每天学习的时间比高中时还要长,一点也不夸张。一开始我还以为是自己考题不够好,后来,我向其他同学请教学习,发现自己没有掌握相应的学习方法。
难度的另一个方面体现在课程足以“颠覆三观”。 比如,作为天文学的基础课,“四力学”就包含了量子力学等内容。 “研究之后,我发现我之前的很多理解都是错误的。” 赵珊珊说,天文学使用的是另一个与日常生活不同的系统。 用于解释和研究宇宙的语言,第一次接触它就像学习“一门外语”。
天文学中有许多未知领域有待探索。 因此,不仅在学习上,而且在科学研究上,天文专业的学生都面临着很多问题。 “很多时候我绞尽脑汁也想不出解决办法,常常会在一个问题上卡上好几天。” 上海交通大学天文系博士生徐坤感叹道。 他表示,这个时候,他会暂时研究一下其他话题,回头看看,也许有些事情会变得更清楚。 “实际上,我解决问题的很多想法都来自淋浴和睡觉前等时刻。”
谈到天文研究的不确定性,徐坤的同校同专业师姐、今年即将博士毕业的胡丹也感触颇深。 撰写第一篇学术论文的过程也是她迄今为止在科研中经历的“最大磨难”。 这篇论文相关的科学研究从2014年开始,一直持续到2018年。论文提交后,审稿人回来了很多严肃的意见。 根据大家的意见,她花了半年时间修改论文。 然后她又给审稿人第二轮意见修改,又花了半年时间。
这篇论文历时5年才终于发表。 胡丹直言“直到修改结束我都麻木了”。 不过,她在论文中所付出的努力,让她在天文学方面得到了很多基础训练,也拓展了她的知识面。 “学习天文学的时候,你要调整心态,保持一颗平常心很重要,这样,你研究中的每一个小小的突破都会给你一种成就感,这会给你坚持下去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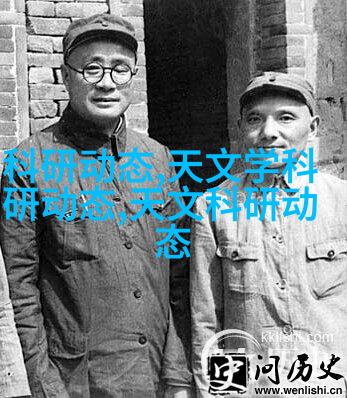
一方面,天文学的学习和研究需要年轻人能够耐得住孤独,因为很多时候你可能独自一人在电脑和数据面前,从白天学习到晚上; 另一方面,它需要你有很强的技能。 团队合作能力,以及跨国界、跨文化的合作,因为当今天文学前沿领域的研究几乎都是以大型国际合作项目的形式进行。
“本科、硕士、博士期间出国交流、参加国际联合培养项目几乎是天文专业的‘必修课’;而博士毕业后,这也是我们参与国际合作的常态路径” “项目团队通常有数百人,来自世界各地,如果你太害羞,不善于沟通,很难想象你能从项目中获得多大收获。”胡丹说道。 按照计划,几个月后她将前往捷克,加入国际天文研究团队,开始博士后工作。
天文学的浪漫与现实
虽然学习天文并不容易,但年轻人为了自己的梦想和兴趣,还是走上了这条道路。
2018年,王佳琪报考了物理专业,进入物理与天文学院。 入学后,她在一门天文学通选课中接触到了天文学的奇妙。 大爆炸理论、暗物质、暗能量……这些让她充满了好奇,点燃了她的兴趣火焰。 于是她申请转专业,大一下学期,她就成为了上海交通大学天文系本科首届的一员,也是七人中唯一的女生。
当她的父母听说她选择转读小众专业时,有些担心,并试图劝说她。 “我坚持了,希望能一直保护好自己珍贵的好奇心,相信会有理想,会有面包。” 王家齐说道。 在她眼里,天文学的“浪漫”并不是常人理解的“浪漫”。 “我的研究项目处理的是平凡的数据,但从平凡的数据中解读出不平凡的意义,才是真正的浪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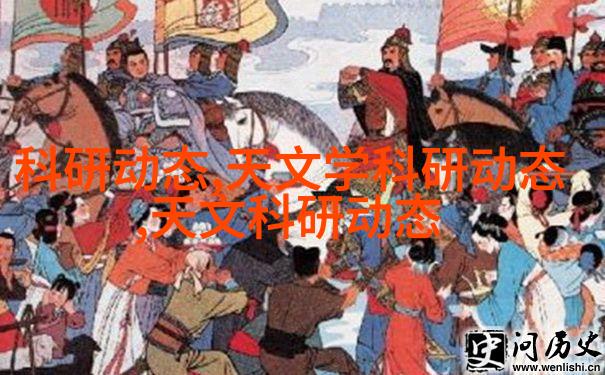
而且,她希望将来能成为一名天文老师,虽然她觉得实现这个目标并不容易,因为“我们不能让学生误入歧途”。 “我在课堂上经常受到老师的一些想法的启发,我希望以后能和学生分享我的想法,虽然可能还不成熟,但足够有趣,让他们喜欢上天文学。”
胡丹本科时也主修物理学。 大三的时候,她整天泡在图书馆,读了很多天文领域的书籍、电影和科幻杂志。 她对天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在硕士和博士学习期间主修天文学。 现在,六年的天文学学习即将结束。 她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像在图书馆时一样,她对这个学科仍然保持着浓厚的兴趣。
“现在的年轻人有很多选择,没有人注定要学天文学。但我因为对天文学的强烈热爱而选择了天文学。我和我的同学大多都是这样。”这种热爱也是一种的浪漫。
当然,你还是可以通过研究天文学来观察星星。 赵珊珊大二的时候,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刚刚竣工,很多基础设施建设还在进行中。 学校天文台所在的小山当时还在校园墙外,周围都是建筑工地。 实践测试课总是在没有明亮月光的晚上进行。 她和四五个同学组队,打着手电筒,在黑暗和寂静中沿着小路爬上山,就像是在进行一场野外探险。 当我们到达山顶的天文台时,我们常常要观察一整夜,有时甚至通宵达旦。 虽然我们很累,但是也很开心。
她还登上过紫金山南京大学太阳塔。 这座建于40多年前的塔式望远镜的墙壁上爬满了常春藤,给她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 大三时,她参加了澳大利亚一所大学的交换项目。 她戴着安全帽爬上垂直的梯子,第一次看到了大型射电望远镜。 她非常震惊。
然而,并不是每个天文系的学生都能有这样的经历。 胡丹研究天体发出的X射线波段的电磁辐射。 由于大气层的阻挡,这些电磁波无法到达地面。 所有观测它们的望远镜都是太空中的卫星。 “用研究数据源的望远镜拍照”和“操作望远镜看星星”对她来说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胡丹说:在学习天文学之前,她并不经常使用电脑,但现在她走到哪里都要带着电脑处理数据,经常从早上8点到晚上11点盯着屏幕“有时在回国的路上”深夜从实验室回到宿舍,我仰望天上的星星,心想:如果我的使命就是这样看美丽的星星就好了。但是,我还是要回到现实。就像那些美丽的星星一样。原始的天文图片实际上是黑白的,而进一步的来源只是一些数据的矩阵。这些来源的基础研究工作必须有人来做。”
许多天文学专业的学生选择继续深造,攻读博士学位,然后从事科学研究工作。 这意味着她们进入社会较晚,家庭“逼婚生子”的压力相当大,尤其是女性。 。 “在学校的时候,我专注于研究,没有时间恋爱;当我参加博士后项目时,我可能不会每次都在同一个城市,甚至同一个国家。不可能安定下来,而且组建家庭是不现实的。” 赵珊珊讲述了她面临的实际问题。
但如果真的“无法继续读书”,这个小众专业的学生就业适应能力并不窄。 徐坤说:天文学的基础课是数学、物理和计算机。 只要你认真研究,转相关领域并不难。 比如金融行业很多工作其实就是数学分析,而天文专业获得的编程能力足以支撑在互联网大公司做“码农”。 这些都是薪资普遍较高的行业。 “学习天文学的路其实并不窄,但我怕你会自己放弃。”他说。
天文学教育的未来是光明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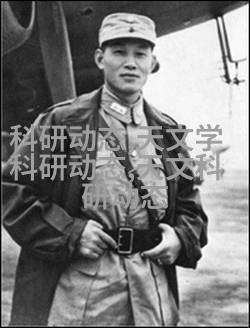
“天文学确实是一个烧钱的学科。” 南京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陈鹏飞表示:天文学研究以观测为基础,观测设备落后是发展缓慢造成的我国过去的天文学学科。 一个重要原因。 近年来,我国科技实力取得长足进步。 从“悟空”、“慧眼”卫星的发射,到“中国天眼”FAST的建成,我们在硬件领域一直能够走在世界前列。
同时,经济社会的发展也让更多人特别是年轻人接触到天文相关的科学。 我国的天文爱好者越来越多,水平也越来越高。 学习、了解天文学的氛围逐渐浓厚。
我国天文教育现状如何? 截至2020年,中国大陆共有22所大学正在较大规模开展天文教育和研究。 其中,12所大学拥有天文学本科专业,7所大学拥有一流博士点,9所大学拥有一流硕士点; 目前,每年天文学专业本科招生总数约为200人,在校学生总数约为2700人,其中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各占三分之一左右。
与英国、美国相比,我国大学天文教育规模较小。 英国人口只有6600万,是中国大陆人口的二十分之一,但可以授予天文学学位的大学约有48所,是我们数量的四倍; 美国有3.3亿人口,还不到我们的四分之一,但是他们有161所可以授予天文学学位的大学,比我们多了十倍多。
“从这一点来看,我们的天文教育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陈鹏飞说道。 他担任秘书长的教育部天文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也一直在鼓励和协助更多的大学设立天文系或天文专业。
中国的天文教育确实需要扩大,但这并不意味着必须积极进取或达到英美国家的比例。 陈鹏飞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在其他一些国家,天文学领域的博士和博士后已经达到了过饱和的状态,这个群体的就业面临着困难; 中国应该吸取他们的经验教训,在扩能的同时进行分级发展。 、天文教育具有高校自身特色。
比如,我国中小学缺乏专门的天文课程,就源于缺乏专业的天文教师。 “天文知识是地理老师教的”不是一句玩笑,而是事实; 此外,一些天文科普场馆还需要具有专业教育背景的人才。 如果高校能够培养这些方向的学生,那么天文学专业人士可能不一定需要获得博士学位,而且也会有广阔的使用领域。
南京大学天文系成立于1952年,是新中国成立最早的天文系,也是全国顶尖的天文学高等学府。 该系尝试在本科阶段开展差异化教学,根据学生是否有继续天文学科学研究的愿望提供不同的教学计划。
发展符合社会实际需要的天文教育也很重要。 陈鹏飞介绍:贵州省一所大学几年前就开展了本科天文教育。 直接原因是FAST位于学校所在区域,围绕望远镜建设了天文小镇,产生了对文化旅游和科普人才的需求。 。
“科普是天文学发展非常重要的一环,如果有具有较高天文学背景的导游在‘天眼’旁边给游客讲解,将是一个非常有益的尝试。”当时的评审委员会均表示赞赏学校对天文本科专业的设置提供了支持。” 陈鹏飞说道。
另一方面,如果未来有更多的大学设立天文专业,这将为天文教学和科研人才提供更多的舞台; 我国已建成、正在建设和规划的各种大型天文观测设备也将需要大量的天文工作来维护、运行和处理数据。
在扩大容量的同时,教育质量也必须进一步提高。 陈鹏飞从事天文学教学已有20年。 在他看来,当今中国的天文本科生需要增强实际测量能力,这已经是现实的短板。 “如果现在给一个天文学本科生一个有缺陷的望远镜,他能调整它或者提高它的性能吗?如果他能做到,那么我们培养的学生肯定会擅长计算机、光机械、电子学等方面的综合能力。”了解控制和数据处理等方面。” 在研究生教育领域,他认为我们的学生应该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国际合作。 “在某些我们还不太擅长的领域,最好的办法就是送学生出去学习。”
“当我们仰望星空时,看到璀璨的星星,是一种浪漫又美好的感觉。通过我们的探索,我们陆续揭开了宇宙的奥秘,那种成就感和幸福感更是美好。科学之美。我希望更多的人愿意和我们一起体验这种浪漫和美丽。” 陈鹏飞说道。 (记者王宇)